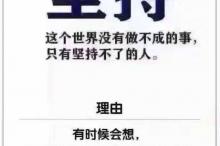太原道上的苏丹先生,为我们证明了触键写作的流畅快感,互动交流的写作延伸。这是一次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写作试验,也是一次行为艺术。苏丹赋予芯片情感,在虚拟世界里重建了故乡。——贾樟柯
龙城之“闹”
作者:苏丹

城市的起源始于贸易和军事的目的,而城市的兴衰变化得益于“闹”。
“闹”是个中性词,褒贬各半,客观地表达着人类在生命和社会中的各种行动。“闹”在山西方言之中是个宠儿,它的含义几乎涵盖了人类的一切行为,就像我们今天口语中已上位的“干”“抓”一般。和“干”“抓”堂而皇之在国家喉舌中反复吞吐相比较,我发现“闹”着实有点憋屈,它始终没有实现自我超越,一直步履蹒跚于乡党的口中,带着浓郁的黄土气味。
但若是表述和三晋大地有关的记忆,描述曾经发生在我视野中的各种人和事件,渲染早已逝去的时空氛围,还非“闹”不可。
除了其动词的词性,“闹”字还有形容词的词性,来比喻环境的热烈、喧嚣等感官刺激。记忆是一部压缩机、一套筛子,留下的都是大事、趣事、怪事,“闹”都是这些事的表象,要么惊世骇俗,要么震耳欲聋。
在龙城的现当代历史中,“闹”的景象此起彼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烟尘滚滚的工业建设,六十年代汹涌的红色波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变不息的时尚大潮。“闹”既是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动因,还是一个城市生命的迹象,它形象、生动,深入人心。
太原人喜欢用“闹”来表达一切,“闹”是一个基本的字眼,每一天它都会汇聚在鼎沸的人声中, 合成这个庞大生命体的呼吸声;它亦如图像中的像素,永不停息地绘制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肖像。
但是如果改变时间的参数放大来看,每一个像素又是历史上醒目的一瞬之间,夹杂着世事沧桑,交织着人间的喜怒哀怨。
远景龙城
九朝古都太原古称晋阳,是唐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之地,故自诩为龙兴之地。龙是兴风作浪的高手,事实的确如此。
这座城市历史上多坎坷,历次被“闹”毁、历次“闹”重建,反复折腾。秦庄襄王二年(前248 年),秦将蒙骜平定太原,次年初置太原郡。前221 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太原郡治在晋阳县。晋阳城相传为春秋末年,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筑。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毁晋阳城。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宋将潘美奏请在原晋阳城以北的唐明镇基础上,“闹”起新的太原城。

晋阳古城与汾河故道
1949 年的那次攻城“闹”得最凶,太原老城巍峨的城墙在这个城市经历的最后一次战争中,被一千多门大炮集中的炮火摧毁了,我上高中的时候看过攻城士兵疾速掠过城垣的战时摄影图片,算是这个城市的前世在我记忆中残留下的仓皇而又匆匆的背影。随后太原城的城垣被陆陆续续拆除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物证,比拆除北京城的城墙更彻底更果断。历史上政治更迭相伴的战争、内乱、外敌入侵造成这座城池在焚毁、荡涤、沦陷、膨胀中反复幻灭,不断重生。物质性的历史在物质的遗失、丢弃、销蚀、毁损中变得模糊,文本的历史在涂抹、篡改、修饰、掩盖下变得可疑。名义上的古都太原渐行渐远,形容越来越抽象,总体看上去几乎像个如郑州和石家庄这样的新城市,在我从小的记忆里就是这样,曾经巨大的物质存在只留下了一个个挣扎的地名:“大南门”“大北门”“大东关”“水西关”“旱西关”“小东门”等,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
如今的太原城,城市形态方面:一座被闹成了一摊,郊区闹成了城市,公园闹成了盆景,工厂闹成了住宅,宿舍闹成了小区,大马路闹成了立交桥,由地面闹到了地上,由地上闹到了地下;
生活方面:面食闹成了米饭、比萨,白酒闹成了红酒、香槟,方言闹成了普通话,大浴池闹成了桑拿洗浴;
文化方面:书店闹成了网吧,俱乐部闹成了会所;
精神状态方面:闹革命变成闹钱。
龙城景中
《闹城》是一部图文对照的个人口述史,它的文化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强国梦和工业化建设。
1949 年后,这个古老的城市被政权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力“闹”工业成了新时期的主要任务。1954 年的城市规划大纲中这样描述它的性质:太原市是山西省的工业中心,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城市。规划到1958 年66 万人,到1974 年80万人;规划了北郊、城北、河西北部、河西中部、河西南部五个新工业区及相应的生活居住区;确定汾河和迎泽大街城市轴线,棋盘式路网。
很快,一条东西向的大街沿着旧南城墙根开拓了出来,这是一条新龙城的横向主轴,在景观上贯通了东山到西山的廊道,在交通上跨越了南北向的汾河。它和那条宽阔但断断续续的河床构成了新太原的架构,显然这是工业时代的气魄——天堑变通途,晋阳老城被甩在了一边。
汾河是龙城的南北向轴线,上游修了水库之后,它成了一条宽大的泄洪通道。汾河的西侧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区,继续向西是煤田蕴藏丰富的西山。随着上游汾河水库的修建和龙城工业化进程,自然的河流也逐渐成为一条工业排污的渠道。河西、河东两岸的工厂将排污的管道直通汾河,每日里烟黄色或深灰色的、带着泡沫的工业废水会从粗大的管道中喷涌而出,为这条干涸的河床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
于是气象万新,一条色彩凝重的大河向南奔流而去,一如它焦灼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