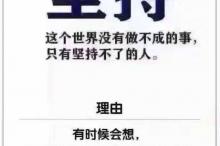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我不是一颗会喘气的瘤子。”北京军区总医院著名肿瘤专家刘端祺的一名病人这样写道。
医学技术的理性,包裹了病人需要的温暖,临终就变得冷漠而残酷。“技术至上”的流行,常使得医者忘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总有人想努力弥合这种技术与人性的鸿沟,叙事医学这时候就出现了。120多位临床医生,口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临终事件,讲述死亡之前的希望、亲情、残酷,使临床医学更富人性、充满温情,有助患者治疗。
这些情感复杂的临终事件,被编进《死亡如此多情》这本书里。
“我想和你一起一直到最后”
“不管是快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患者,还是他们的家族,确实富有一些特别的情感。”7月31日,围绕此书所涉及的话题,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与本书的策划者及医学领域人士进行座谈,反思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以及如何让医疗过程更有温情。
韩启德说,亲情、爱情、友情都会在这一特殊时刻展露得尤为明显。
2012年7月23日,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工作的闫刚(化名),向到访者程蓓细致地描述起一个“葬花女孩”。那时闫刚在脑外科实习,患有小脑胶质瘤的15岁女孩张希(化名),住进了闫刚导师分管的病区。
多天时间里,每当张希要接受检查化验,都会以各种理由支开自己的母亲。闫刚慢慢明白了张希的用意和坚持。有一次张希看到母亲离开,自言自语: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做检查的样子。
张希喜欢跟护士聊天,闫刚从护士口中得知,她从小没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所以闫刚偶尔会配合她撒个小谎。
张希并不知道,母亲每次都是假装离开,再悄悄地跟在后面看她做检查。
闫刚说,“在MRI(磁共振成像)室外,她妈妈告诉我,‘其实,我知道她不想我看见她检查时的样子,怕我伤心,我都知道。’”
在闫刚的记忆中,母亲面前的张希,乐观活泼,爽朗的笑声总在病区回响。但这不是她的真正的快乐。
一天,坐在医院花坛边的长椅上读书的闫刚无意中看到张希,她正在草丛中捡拾掉落的花瓣,挖土坑埋掉。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希对闫刚讲出了实情:自己并不开心,那些快乐都是装出来的,她只是不想让母亲担心。
刚查出病的时候,张希想过自杀,她羡慕别的女孩可以梳好看的辫子、穿漂亮的衣服上学,自己却剃了光头,穿着病号服留在医院。她甚至提到“等死”这个词。这让闫刚吃惊,他不会想到乐观的女孩竟如此厌世。
幸好15岁的张希明白,前后三次住进医院的她,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我是妈妈唯一的支柱,她不能没有我。所以我一定要活,还要活得很健康、很快乐。”
求生欲无法阻止病情发展。经历了两次手术的张希,小脑胶质瘤再次复发,侵及颅骨,成为高级别胶质瘤,恶性度高,无法完全切除,只能采取保守治疗,预计生存期只有半年。
知道这一结果的母女俩有着不同的表现。张希微微一笑后,撇过头去流泪。母亲则跪在地上,求医生再救救她的女儿。
最后,张希扶起母亲,擦去母亲脸上的泪水,告诉妈妈:“我们回家吧。我想和你一起,一直到最后。”
母女相拥离开。
“病人对生命的巨大留恋,亲人对逝者的无限不舍,医护人员的同情与遗憾,是情感让死亡不再那么寒冷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苏小卫,在读完这本书后感慨。
技术的冰冷包裹医生对病人的情感
临床医生口中鲜活的生命、复杂纠结的感情,若不是此次集中表达,患者和家属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
在很多人眼里,冰冷的仪器、冰凉的液体,甚至是医生平静的表情,让医院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地方。而患者忐忑的心情,家属着急无奈的神情,在患者病情宣告不治的那一刻,化作悲痛甚至愤恨。
医患关系的冲突,仿佛就发生在这一刹那:“你们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吗?”“对不起,我们真的已经无能为力。”
患者家属的大声质问和医生“不近人情”般的劝说,常常是两种对立。北京肿瘤医院医生严雷(化名)就经历了这一切。
成为严雷的病人时,15岁的王宇(化名)已经从骨肉瘤转移为肺部肿瘤。
虽然经过了长达四年的治疗过程,王宇的病情却越来越糟。严雷意识到,即使自己倾尽全力,继续为王宇治疗下去,也可能只够延长他几个月的生命。而且治疗后期,王宇会更加痛苦,王宇的家庭也会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严雷劝王宇的父母“量力而行”。王宇的父母却极为坚持,他们就这一个儿子,咬牙也要治到底。
几个月后,王宇出现了胸水,先是淡黄色清亮的,随后变成血性的,越来越多。严雷意识到,这是病情进入终末期的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