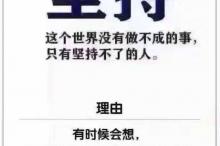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世的变迁,心态的炎凉,很多的朋友说,对于年渐渐失去了热情,觉得年就是个忙碌,就是个累。可我还是喜欢过年,喜欢纱灯的颜色,喜欢对联的祝福,喜欢门神的威严,喜欢看人们的笑脸,喜欢听鞭炮的炸响,更喜欢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喜欢母亲的压岁钱,喜欢饺子里那枚吉祥的钢蹦。
进了腊月,就盘算着买这买那,东西很多有时候就忘记了一样两样,可是有一件事无论怎样忙乱都不会忘记,那就是给逝去的亲人上坟,去祭奠他们。我家的祖坟在很远的乡下,小年前和妻、弟弟弟妹还有大侄雇了台面包车买上黄纸,冥币,金纸叠的金砖去给祖先上坟,今冬雪大,田野上一眼的洁白,雪厚得看不出哪是垄沟垄台,哪是平地沟壑。坟地在一坡向阳的山坡上,积雪没膝,抱着黄纸一步一踉跄,可心是定的,眼光是温暖的。为那些我的前辈,我相识或者陌生的亲人,流年暗渡,古柏依旧肃穆,流云依旧匆匆,而纪念永恒。
回想去年,对于我的家庭是苦难的一年,老弟在哈尔滨突然生病,妹夫也在大庆遇了车祸,都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万幸的是他们都挺过来,我想在冥冥中在他们的内心都有一种超乎于生命的坚持,那种坚持就是爱和责任。我说过,他们的苦难日也是我的。骨肉相连的兄弟,我们彼此都不能缺少,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如同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伤了哪枝枝桠,树都会痛。春节前,我邀请他们都回家过年,他们都快乐的回来了,看到四个健康活泼乐观上进的孩子,我把他她们拥抱在怀里。
小年一过,就和弟弟妹妹到敬老院来接叔叔,在敬老院并不干净的窗外,就看见叔叔爬在窗上在向外看着,我的心真有些疼,弟弟说,叔叔就活在这样的期盼里。回到县城,弟弟领他在浴池洗了燥,理了发,看见干干净净的叔叔,脚步虽然吃力艰难,看着叔叔的笑脸,我知道这个年我不缺什么了。
年时,音信阻隔51年的母亲叔叔家的舅舅从辽宁寻亲而来,我们一家三十多口人聚集在一起,老人家64岁了,在酒席之间,老人家给我们唱了首《我的中国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他说,他十三岁的时候来过黑龙江,来看大伯大娘(我的外公外婆)。那时侯大姐(我大姨)已经在供销社上班,二姐(我母亲)还在中学读书。他走的时候,我的外公还给他炒了二斤半的玉米花,他说,那玉米花很香很甜。那种滋味让他记忆一生也回味一生。大姨给了他五斤全国粮票。他就靠着这些在当时很奢侈的东西走回了辽宁,从此失去联系。51年让舅舅魂牵梦绕的亲人,今天他终于宿梦得圆,长思得现。老人家高举起杯,高呼喝酒!我们一起呼应着,喝酒!
人到中年有些人生的祸福让人措不及防,年初二的傍晚当我正兴致勃勃的和家人朋友节日小酌的时候,女儿打来电话说她姨奶家的大伯生病住院,当我急忙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的兄长已经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年仅48岁,故于心梗。兄长平日少言寡语不善酒席,默默的做着他工地上水暖生意,几乎年年被三角债拖累,不得喘息。去年干了六份活,等到大年二十八九才回来,可还有四份的工钱连电话都打不通,也许郁结在胸,不得畅怀。一言未留撇下了刚刚成家的侄女还有悲痛欲绝胆小的嫂子。朔风野大,我们安葬了兄长,深雪皑皑,花圈肃穆,伤心几许!在回去的路上,我回头再看一眼,田野洁白,兄长却永远的躺在无数的花圈下面,象一朵花开。春天就要来了,兄长却默默的走了,泪水又一次糊满我的眼睛。
女儿从学校放假回来还特意给我买了两本书《契可夫短篇小说精选》、《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我的心是温暖的,可女儿哪里知道,过了年爸爸就很少有时间能静下心来读书了,那些宁静而美好的时光被生活的琐碎所占据了。女儿说,等叶子黄的时候就可以读了。我笑了,知父莫如女啊。女儿说,她们学校的霓红牌上,闪动着高考倒计时,她很紧张,时常头痛。看见女儿真的有些瘦了,心里一半是怜爱,一半是鼓励。毕竟今年是她决定命运的时候。对女儿说,首先我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女儿,你努力学习,爸爸努力工作,我们一起奔跑。
岁末的太阳暖暖的,地气在酝酿,春天正在回来的路上,在安静里断续地进入这些往事,宇宙浩淼,世道流转,生活,我的亲人离我或近或远,这样回想的时候,似听到他们的欢欣或叹息,看到他们的笑脸或愁容。
窗外,有凌凌的风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