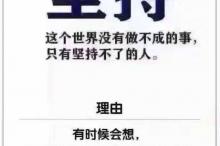世界上没有哪个部门这样强大,三拳两脚就把人的心和肉体同时给收拾了,不管你是王孙贵族,还是千金小姐,更何况那有限的拳脚里包含多少假招数还显得如此底气不足,如此的差强人意。
第一次庄严地走进这座高大的建筑,各种五花八门的指示标识搞得你晕头转向。疾病像一个魔杖一下就打掉了你紧握生活的手, 让旋转的玻璃门快速地旋转——皆为病来,皆为病往。
我穿梭在雾霭一般的白色帷帐中是看望我的亲人——我唯一的哥哥,他风华正茂,有着铁塔样的身坯,在一个子夜,就轰然倒塌了,他被推到了这个常人不到的角落里,老老实实地被俘了,不是被情,被爱,而是就让一个叫病的魔爪擒获。
在观察室里一共躺着十个病人,上帝就这样十人一拨地把他们叫来训话,并给点体罚,鼻子上、手背上、脚上都插满了皮管子,给氧、仪器检测,像是做着复杂的人体实验,不管是否行之有效,所有的医疗仪器要在每个人身上发挥最大的功效。白衣天使们手上没有箭,却在脆弱的肉身上射入一根针,针后是一根细长的管子,拖着沉重的药水瓶子,瓶子里的水一滴一滴,就像雨露滋润着禾苗,渴望枯萎的生命得以复苏。
我的目光在这样一群人的脸上扫过,男女老少,品种齐全,却一律手脚被绑,身萎病榻,如囚在牢。死亡的可怕人人皆知,我们可以做各种假设期待那样一个节日的降临,然而更加可怕的是当你跃跃欲试,当你摩拳擦掌,当你春风得意要快马扬鞭之时,忽然一场疾病的秋风杀气腾腾地将你撂倒,叫你停顿停顿,将你折磨折磨。
这个四十六岁的女人进了病房再没有睁开眼睛,她的脸一直向着天花板,似乎在背诵天花板上的那本奇书,她是在穿戴齐整了准备赶赴一场婚宴前忽然倒下的,她的妹妹始终摩挲着她的手,不停地在她耳边呼喊“二姐,二姐”,她没有回应,那仅存的可怜的亲情唤不起她丝毫的记忆,病魔就那样坚硬地阻挡了血溶于水的姐妹情深。男人还算是优秀的,男人坐在小板凳上耐心地将菠菜胡萝卜剪碎,尔后做成菜汁,他要通过鼻子注射的方法维系女人的生命,我看到了他眉宇间因疲惫凝聚的一丝酸楚,天晓得,他要陪自己的女人走多久!
战争影片看多了,觉得受伤流血并不可怕,然而看到一个人血肉模糊地在眼前,还是心有余悸的——他让你知道生命的脆弱。这个五十岁的男人简直就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准确地说,是从生活的战场上败下阵来的,他被一辆汽车撞到了,他的头颅没有抵挡过金属的硬度,鲜血模糊了他整个脸颊,一只眼睛终于被粘乎乎的液体淹没,看到不到他想看的世界了,其实,没有那个拐弯,没有那辆轿车,那一天,他是蛮高兴的,他洗了澡,打着胡哨,要和朋友小聚一次的。然而,宇宙间没有静止的事物,无常,就像牛顿的自由落体——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这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微笑,疼和痛似乎拿她毫无办法,她是唯一病着并且幸福者的人,她没有老伴,孤苦伶仃,做了一辈的护士,老来需要别人护理,因为生病两个儿子不得不从外地赶来,儿子耐心地往她嘴里送南瓜饼,她嚼的很慢,生怕幸福的滋味不小心在嘴里溜掉了,孙女叽叽喳喳给奶奶讲故事,她歪着头尽管嘿嘿地笑,儿媳是一张娃娃脸,围在身边像个乖女儿,收拾老人的大小便也不嫌脏,老太太心中的欢喜已经已经溢得满满的了,真的不敢想象她痊愈后的那场凄美的离别!
护士小姐表情默然地在病房里行走,她们漠然的态度是值得理解的,莫非人家还要陪着病人呻吟不成?只要是有病的躯体躺下,即便成了可怜之至的羔羊,哪有鲤鱼躺在砧板上还要与厨师聊天的道理,我是亲眼看到一个带着口罩的大眼睛护士,掀开一位男性病患的被子,从容地实施她的导尿术,不管患者怎样的挣扎,她依然表情凝重,做得有条不紊,我第一次对这项职业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灵台无计逃神矢”,既然无处可逃,就安静地躺着,然而,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张床,那长长的一串缴费清单,像沉重的一个秤砣,坠在你心的杠杆上,病患糊涂着最好,将危机感转嫁给家属,盘中的青菜炒肉,味同嚼蜡,一场病,对某些家庭来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它要把你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甩出来,你就像从高速公路上被挤下来的汽车,你的生活秩序完全乱了套,病就是要剥夺你正常生活的权利,是否要剥夺你生的权利,观察一下,看看你的造化如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