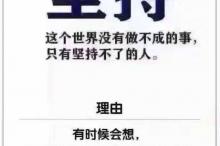太阳爬上第二个窗格子的时候,哥已经像猴子样从小窗口钻了出去。
我和妹妹 眼巴巴看着哥越过木栅栏,站在墙头向我们摆手:等着,哥给你俩捞鱼去! 哥一准去找后院的大军了,哥不会捞鱼,哥的能耐是替大军扛水桶。
回来就告诉妈妈! 妹妹毛绒绒的眼睛里已经有泪水在打转转,我和妹妹都将小脑袋探出窗去,目光愉快地追赶着院子里的两只蝴蝶,蝴蝶飞累了就伏在黄瓜架上打盹儿,大把大把的阳光金子样在眼前泼洒。忽然,天上有了隆隆的声响:飞机,飞机!一个银灰色的庞然大物划过天空,我和妹妹一边拍手一边扯着嗓子高喊:中国飞机加加油,美国飞机掉粑粑楼!
飞机摔下来会很疼吗?妹妹眨着好奇的大眼睛。
管它呢,太阳已经用发光的彩笔在炕上划出了齐整的六格,拳头大的青苹果在我们脚下变着法儿似的滚来滚去,待滚得像泄了气的皮球时,我们便放在嘴里啃出两排兔唇一样的牙印。
炕头的面盆用花格子的小被捂着,我们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小手在面团上摁摁,一会儿就摁出乱七八糟的爪子印。外面传来英子妈破锣似的喊声,我和妹妹把翻烂了的那本小人书拿出来,我们指着书上的周扒皮说,英子妈就像那个老东西,不然每天怎么像公鸡打鸣一样那么早就伸着脖子叫唤呢?相反,裙子妈才是大大的好人呢,裙子妈隔着木栅栏把地瓜干塞给我们,还要在我们的脸蛋上掐一把,裙子妈的声音才叫好听呢,咯咯的笑就像一串铜铃在响,裙子新穿的花棉裤尿湿了妈妈也不恼,裙子妈慢声细语数落着:一回两回怪妈,三回四回挨掐。哪像妈妈呀,哥哥用水笔画了两回地图就大呼小叫大的。
唉,哥哥的鱼不知道上钓了没有?
墙上三五牌的挂钟敲过四下,敲出了妈妈下班的时间,战场囫囵地打扫完了,两双小眼睛迫切地盯紧妈妈手里鼓溜溜的帆布包,那就像魔术师的魔毯,抖出的红枣、青杏、毛桃尤其是香喷喷的核桃酥,总令我们垂着三尺长的涎水。
妈把炒熟的花生喷上几滴盐水,上面就挂了一层白白的霜,每人一羹匙,不多不少,轮到哥哥时,我听到了饭勺子敲击锅沿儿的愤怒声儿。
哥的样子实在太狼狈了:海魂衫扯出了长长的口子,胶鞋上粘满了黄泥巴,鼻涕像一道水柱在嘴边吸溜……不用问,不是爬城墙,就是又给人扛水桶了!妈这次没有动用任何武器,比如笤帚掸子等等,而是像拎小鸡一样把哥拎到了院里的杏树下,不容分说,五花大绑就结结实实把哥绑了,哥昂着头,像个英雄。
我和妹妹捂着嘴吃吃地笑。
妈严厉的目光转向了我和妹妹,园子里四根黄瓜明显少了一条,这桩悬案还能跑了你们两个小妖?妈像侦探一样盯着我们的手,窄窄的栅栏容不下我胖乎乎的拳头,妹妹两只小鸡爪子背在身后,抿着嘴,死死地抿着,终于“哇”地一声哭出来。泪人一样滚到妈妈怀里。
灶台前,金黄的玉米饼在妈的手上来回拍打,瓜达瓜达的风箱拉出好听的节奏。我一边往灶膛里添火 ,一边聆听妈妈的教诲: 少跟裙子那臭丫头鬼混,她妈就不是好东西!瞧她走路时的浪样!怎么会呢,裙子妈是多好的一个人呀!真的猜不透大人的心思。
妈临出门时将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地震真的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大人们再不敢锁住我心中的小兔子。妈妈每天分配给我们三样活计:抬水,剁鸡食、拉风箱,活计做妥当了就可以到刘老爷的后院去耍了。
我、英子、老民猫着腰,悄悄靠近刘老爷的葡萄树,我们把小文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些日子我们都传伙孤立着小文,原因是小文有一套彩色的羊子儿,也就是羊的后退上的一块小骨头,这个小气鬼藏在胳肢窝里就是不给我们玩,哼,臭你几天,看看还有啥脓水?孤立的结果是,小文已经苦着脸,嘴厥得老高,估计明天她就耐不住主动献出那套宝贝了。
刘老爷的唢呐已经传出好一阵子,吹得像一个人咿咿呀呀地哭,大人们说,刘老爷一吹唢呐就是和刘姥姥吵架了,他总是怀疑刘姥姥外面有人。外面有人就请到屋里来嘛,干嘛要动手打刘姥姥呢?真的是老糊涂了。
茄子还没长成,像鸡蛋一般大,我们不摘,而是小猫一样趴下来,在每个茄子下面咬一口,咬成一个弯弯的月亮,然后悄悄地向葡萄树逼近……
趴在树下的大黄警惕地竖起了耳朵,老民脚底绊倒的石头终于让它发出汪汪的叫声,唢呐嘎然停止,刘老爷气急败坏地趿拉着鞋从屋里窜出来,扯着粗嗓就吼:小兔崽子们,让我逮住摘除你们的胰子!
我们仓惶地顺着墙根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