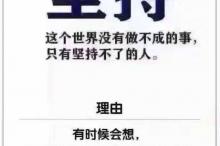他的朋友都说他“很傻”,有些时候就是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老掉”并不是他的真名,只是叫的多了又没有不雅之处,也就用开去了。他人不高,纯属三等残废之列,长的还算墩实,满脸横肉的顶上留着短短的的头发,据说从小时候起就是胖墩,不过走起路来倒是风风火火的,寻常人家很难追的上,远远望去恰似一个滚动的肉球,特别是在冬天。长着一张绝无仅有的平平常常的脸,还有点麻,大大的鼻子下,一对鼻孔显得特别大,逢人便笑,每每会露出两黄黄的大门牙,只是“傻傻”的他,倒也很少看到有搭上烦心事的,就是有,一般也是很难看的出来,也许这就是“傻”的好处吧,在他的心里很难找到“恨”字。有时侯说起话和做起事来就象“天马行空”般,让人感到特傻,也只有这时候,在不经意间也会让人捕捉到一丝的忧伤,他时常自嘲说那是伪装,我却感觉的到,他的真言就在其中。关于他那难懂的绰号是有典故好考的,不过要追述到很久以前,那是后话,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言归正传,该老掉登场了。 ?
那一年,老掉的单位要拆分,话可要说清楚,免得引起误会,可不是老掉要求拆分,他没那个能耐,说笑呢,那都是上头的指示,至于为什么要拆分咱就不得而知了,就算是老掉能看到的最大的头目也是不敢说拆分的,要知道,那是要增加好多大大小小的头目的。某天,老掉照旧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打理他的钳钳锤锤,盘算着今儿该轮到去哪座山里去转转,可别怀疑,那就是他的工作,当然,话又说回来,有时侯顺便去哪个山沟沟里去逛下,看看风景、摘些野果子尝尝鲜或是躺在哪个不知名的山窝窝里的稻草堆上晒太阳,和花花草草小虫虫之类的说说心事是有的。就在老掉盘算的时候,一阵再熟悉不过的脚步声从远及近,老掉头也没抬,他知道那是头目来了,照例是要吩咐一番的,千遍一律地交待交待注意事项,诸如“吃了饭要记得索要发票”之类。头目倒也实在,说是要了发票就是给国家赚回了一些税收。老掉这次却没听到训话声,只见头目递过来一张表格说:头叫你填上,说是让你去乡下“休养休养”几年,不过还要考过场。老掉应了声接过来,看都没看就往抽屉里一扔又继续自己的事。接下来一连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天,以为没自己事了,其实老掉嘴上没说,怕拂了头的美意,事实是没打算去的。他知道,象自己这类人是不大适合走那条道的,咱“视力”不好,又没处学会抵挡和格斗,走起来太累,再说女儿才八个月大。说真的,不是学不会,他就从来没想过要学那些。可没过几天,头目就隔三岔五地催来,甚至头头也打了好些电话来帮助分析,说是如何如何地好,一定要去。老掉整不明白平时只是见面打下招呼的头这会儿咋就这么坚持,不过他知道,事儿是推不掉了,再拖就显得不厚道还会得罪人,也许日后还会没得好果子吃,只好回家商量着权衡下厉害关系后工工整整地填好表格,签上大名之后恭恭敬敬地交到办公室去。好在老掉自打学校出来还不算久远,和些许普通理论还是没有绝交,心里想着既然自己牵扯上了也不能落个难看的结局,更是给头的一个交代,于是顾自找了些书来和女儿一同在那咿咿呀呀地念上不表。接下来就不细述了,考试、三头会审,末了头挑了个良辰吉日把老掉送到山头上,细细地交代了一番后就扔下老掉在那独自看风景经自带着随行的大小头目下山去了。就这样,老掉稀里糊涂地“连升三级”做上了一个山沟沟里的小小的头目。 ?
虽然是在山顶上,但拜访、请客、酒局是一样免不了的,老掉自折腾了好些天才有喘息的机会卸下那一套从未用过的书上写的如何做好小头目的套路,未曾经历过这种场面的老掉装的倒也像,借着丁点酒量加上大嗓门不时还客串回“老千”终是给应付过去。不时还凭着酒意得意地哼上两句跑调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老掉私下里暗自庆幸,平时得空,把个《官场现形记》整个给啃下来,终于派上了用场。接下来老掉还特意花了百十块人民币置换用了多年的水杯,就是心疼了好些日子。老掉一般是不喝茶的,戏说是茶叶贵,只喝水,还是冷的,就是大冷天也一样,平时就都称它为水杯。老掉就是觉得也该显摆显摆,也不是真讲派头,老掉心想,心疼归心疼,总不成整天捧个缺了口的水杯啊,自己的面子事小,可不能失了头的体面。只是老杯子也是舍不得丢掉的,毕竟风里雨里跟了自己那么多年了,便抽空把它洗的铮亮后恭恭敬敬地红布包上收藏起来。还托人买了枝打折的钢笔,英雄牌的,在太阳下还闪着金光,老掉不时一个人偷偷地站在镜子前正儿八经地把个钢笔就着洗得发亮的上衣口袋插上又取下,细心地考究了一番,终究觉的别扭,也难怪,平时看惯了钳钳锤锤的,一时半会儿也适应不过来,只好把钢笔给闲置起来,再也没见拿出来炫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