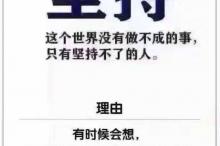原标题:高国森琢磨地道北京话上瘾

吃完了午饭,69岁的高国森跟老伴儿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午茶剧场”,演的是《生逢灿烂的日子》。这是近来收视火爆的京味儿电视剧,但高国森这个老北京还是看得不尽兴,“比起现在这电视剧,人艺的话剧那京味儿才叫浓,才叫过瘾。”
这个普通的北京老头儿,却有个不普通的身份。就在前不久,网民称他为“说北京话最标准的人”,他的北京话最地道。
而他的“官方”身份应该是“北京方言发音人老年男性代表”。2013年,高国森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研究所完成了北京方言的录音。从那时起,从他口中说出的1000个单字、1200个词汇和50个短句,就作为标准北京方言被采集和永久保存下来。
自谦只是做了点儿小贡献的高国森,经过这次方言采集,对北京话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我原来一直以为我说的是普通话,经过那次录音,才知道我说的是北京话。在跟北京语言大学张世方老师这些个专家交流后,我现在明白了,北京话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些词儿现在根本不怎么用了,这就是顺应社会发展。我觉得北京话值得保护、保存,但强行推广就没必要了,语言毕竟是用来交流的,别用方言把咱们封闭了。”
北京话发音人遴选
条件一个不能少
高国森是2012年底开始参加北京话发音人招募和遴选的,当时老年组需要满足的几大条件——1941年至1950年间出生、当地出生成长、未在外地生活两年以上、父母和配偶须均为当地人等,他都满足。虽说被选上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但在老北京南城长大的高国森,打小儿就沐浴在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中。
“我们家至少从我姥姥的父亲起,就是北京人。我小时候住在南横街附近的兵马司前街,那地方已经没了,现在叫中信城。”这座老南城的胡同大杂院儿,外院儿是个装订厂叫荣记,里院儿住的都是普通劳动人民。“有蹬三轮儿的,有焊洋铁壶的,有做苦工的。那时候做苦工的也有好多外地人,不过大家语言交流都没问题,有点儿口音而已。”大院儿里孩子不多,乖巧的高国森备受怜爱。“也没什么玩儿的,我记得去了人家就钻被卧垛玩儿。”玩儿的是被卧垛,吃的是窝头贴饼子。“一个人,好比有三十斤粮票,其中有十七八斤粗粮、七八斤白面,剩下一点儿大米。”
高国森家算比较富足,有台木质的收音机,爱听曲艺节目的习惯就是打那时候养成的。
8岁那年,高国森家搬到了铁门胡同,同样是一个大杂院儿。“铁门胡同那个院儿也是个装订厂,叫久安。久安和荣记合并,变成了北京制本厂一分厂,厂子搬去了兵马司前街那大院儿。我们原来住兵马司前街的那些人就搬到了铁门胡同。铁门胡同这个大院儿主要是印刷工人的宿舍,印刷工人都是北京人,回想起来,应该是说的老北京话。”
出铁门胡同南口,就离菜市口不远了。孩提时代的高国森经常去那附近玩儿,“有个‘毫年堂’,比同仁堂历史还长呢,门脸跟衙门似的。那时候叫‘西毫年堂’,后来改叫‘毫年堂’了。”高国森说的“毫年堂”,其实是“鹤年堂”。“哎,我一直读‘毫年堂’,这鹤不是多音字吗?”
高国森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还是每到春节,舅舅送的“老头儿花”。“一种小呲花儿,泥做的一个小老头儿,头顶上有点儿(火)药,也就能呲一米来高,几秒钟就完,每年三十儿晚上,就盼这个。现在,早没这玩意儿了。”
“街坊”一词
还有好几种区分
“有很多年轻人,老喜欢说怀念过去、怀念老北京。其实我觉着啊,怀念是一回事,过去又是另一回事,以前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特别贫乏,哪儿像现在啊。”
他还记得铁门胡同大杂院儿,西屋有个老太太,经常叮嘱家里孩子:“小二啊,记得买红糖,别买白糖。”为什么?“红糖便宜啊。”东屋那家,有俩印花儿的大暖瓶,舍不得使,当花瓶在家摆着。
“这些啊都是老街坊,现在还有一个,也七十了,跟我还是街坊,我俩还经常喝酒呢。”说起街坊,高国森科普起了北京话关于“街坊”的几种区分。“‘街坊’比较笼统了,就是邻居。其余还有,比如‘住家儿’,也跟街坊意思有点儿像,就是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叫‘住家儿’。现在经常提的老北京话‘隔壁儿’,多数指别的院儿的邻居,一般说‘隔壁儿张家’,就是那个院儿的张家。还有一种叫‘串房檐儿’的,就是租房子住的租户。‘吃瓦片儿’的就好理解了,就是房东,倒腾房子出租赚钱的。”
在铁门胡同长大的高国森,高二的时候去了京西煤矿,当了八年半的煤矿工人。“我在京西煤矿的南片儿,房山。”学生出身的高国森和同学们一起戴着白帽头,其他工人是黑帽头。矿工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异,不过总体上没有交流障碍。“我们倒是跟房山人学了几句房山话,都说北京儿化音重,到那儿才发现,房山的儿化音更重。人家不叫‘叔叔’,叫‘收儿’,特有意思。”
北京话里的
那些讲究与门道
从房山回来,高国森在手扶拖拉机厂工作,直到退休。“我一个没任何特长的人,没想到,2012年、2013年,能给北京方言保护、保存做了点儿小贡献。我跟老伴儿说啊,我这也算没白来这一世。”
2012年底,参加北京话发音人招募和遴选,高国森认识了方言专家张世方,加深了对北京话的理解。“真心话,我说了快70年了,一直觉得说的是普通话。比如,说‘我们’,我真没注意自己说的是‘们’,我就以为说的是‘我们’呢。这些话都是刻在脑子、融在血液里,脱口而出。”
“记得去北京电视台,栏目那时候还叫‘生活2012’,导演说让我准备四天。那四天真是没法弄,到底准备什么我并不知道啊。导演说,主持人是个小女孩儿,让我用北京话夸夸。我说,这可来不了,按北京老理儿,大老爷们儿不能夸姑娘,有点儿不合适。只有老太太能夸姑娘俊、好看。后来,主持人是阿龙,才省了这麻烦。”
2013年,高国森参加音频录制,之后又多次与方言专家接触,自己也越来越留意北京话的变化。“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喜欢收集一些北京话放在网上。我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好,但有些确实有猎奇的心理,有的是想标榜点儿什么,但用的又不是都准确。”